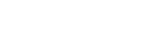于是,孔子从探讨社会、国家领域的“群体之善”,进入私人领域,探讨“个人之善”,即“克己” 。孔子明言“克己复礼” 。学界对于“克己复礼”虽有争议,但都未曾否定礼的复归乃是自身修养过程的体现 。礼不仅仅是作为“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修养自己的一种媒介” 。当儒者通过礼的自身修养从而进入政治生活来规范制约统治者的行为时,“‘克己复礼’的短语不仅是一个‘私人的’道德律令,而且是一个有关儒家公民行为的政治教育的‘公共的’原则” 。同样,当儒者通过礼的修养而进入社会生活中,规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咸在鹤学者的断语同样适用,换言之,“克己复礼”是儒家视域下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 。贺来先生说:“一种价值规范要获得普遍性,必须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遵循,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约束力量,也就不可能成为普遍性的价值规范 。因此,这种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不可能从‘个体生命’出发形成,恰恰相反,它要求走出‘个人主体性’的视野,并确立‘主体间性’的全新视野 。”那么“克己复礼”能否走出“个人主体性”的视野,而确立“主体间性”的视野,并从此出发建构“生成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之中,在相互承认中不断扩大交往共同体的范围”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理想”呢?
依孔子言,礼的修养的起始处乃是个人行为,因“克己复礼”的起点和主体乃是“己身”,非他人,所以可以说,礼的修养是在“个人主体性”的视野下,是“自我主义”的体现 。众所周知,个体存有差异,这种差异性是不可抹灭,现实存在的,因此仅仅立足个体生命的价值规范不可能成为社会价值规范,社会价值规范乃是基于个体生命而在其间形成差异平衡的结果 。
依此说,“克己复礼”似乎不能够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 。而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对于“仁”,孔子未曾明确定义,而是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孔子答:“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孔子答:“仁者其言也仞 。”(《论语·颜渊》)等等,由此可见孔子是因材施教 。此举也正是他正视个体生命存有差异的事实,试图通过点拨各自的修身之道从而达到大公无私之仁的超越境界,最终形成具有超越性和社会性的价值规范 。
毫无疑问,作为“仁”的承载体的“礼”也相应成为了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规范 。孔子说:“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论语·卫灵公》)“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所以,具有超越性和包容性以仁为里衬的礼,可在任何时代发挥着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 。其二,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此“欲立”、“欲达”之目标,为人类共同之道德价值确立,“立人”、“达人”之可能则正是凡之为人在道德情感方面的需求 。于是,无论从情感还是实践来说,存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绝对划分界线不复存在 。
《大学》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道出了个体之己与他人,与家国,与天下无别同一的思想 。萧公权先生诠释得好:“物我有远近先后之分,无内外轻重之别 。”所谓先后,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个体修身的步步扩展延伸,家、国和天下都非外在于我,而是与我同一,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而此“大一统”之“我”则以“仁”为内核的“礼”为最高外在规范 。于是“个人主体性”在合礼成仁的前提下则成为“主体间性”,或者说,达致“仁”德的个人之善在“礼”的联结规范之下,走入社会,自然形成了群体之善 。鉴于这两个方面,“克己复礼”顺理成章成为儒家视域下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和价值理想 。
推荐阅读
- 批量提取文本关键词,Lookup函数两步完成,还不会就真的out了
- 淘宝客服的工作怎么样?需要具备什么技能?
- 盆栽花卉冻焉了还能活吗?
- 碳纳米管粉末微电极对儿茶酚的电催化还原
- SUMIF函数还有个比他更厉害的弟弟,你晓得不?
- 3.7女生节最靓丽还是这些女生节标语
- 建造一个游泳池需要多少钱
- 怎样判断花卉植物是否需要浇水呢?花卉浇水法则分享
- lady gaga取消婚约是为何?营销方式还是炒作手段
- 天猫报名活动需要哪些条件?如何才能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