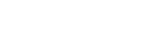家名笔会人的内心并非总是难以捉摸 , 越是那种平常琐碎的场合 , 越是那些胡乱忙碌的行为 , 越是能将其藏匿得不见踪影的底蕴暴露无遗 。 譬如喝茶 , 像我这样固执地喜欢 ,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其是某种指向十分明显的习性 。
在我少年时生活 过的那片山区 , 向来就以种茶和在种茶中产生的采茶歌谣而闻名 。 上学的那些时光里 , 一到夏季 , 不管是做了某些正经事 , 还是百事没做 , 只是在野外淘气 , 譬如下河捉小鱼 , 上树掏鸟窝 , 只要看到路边摆着供种田人解渴消暑的大茶壶 , 便会不管三七二十一 , 捧起来就往嘴里倒 , 然后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扬长而去 。 往后多少年 , 只要这样的记忆在心里翻动 , 立刻就会满嘴生津 。 年年清明刚过 , 谷雨还没来 , 心里就想着新茶 。 那几个固定送我茶的朋友 , 如果因故来迟了 , 我便会打电话过去 , 半真半假地说一通难听的话 。 到底是朋友 , 新茶送来了不说 , 还故意多给一些 , 说是存放期的利息 。
因为只喝从小喝惯了的茶 , 又因为有这样一些朋友 , 使得我从来不用逛茶市 。 外地的茶 , 从书上读到一些 , 有亲身体会的 , 最早是在武夷山 , 之后在泉州 , 然后是杭州西湖和洞庭湖边的君山等地 , 那些鼎鼎大名的茶从来没有使我生出格外的兴趣 , 只要产茶的季节来了 , 惟一的怀念 , 仍旧是一直在记忆中生长的那些茶树所结出来的茶香 。
九月底 , 《青年文学》编辑部拉上一帮人到滇西北的深山老林中采风 。 带着两裤腿的泥泞 , 好不容易回到昆明 , 当地的两位作家朋友闻讯赶来 , 接风洗尘等等客套话一个字也没说 , 开口就要带我们去喝普洱茶 。 汽车穿越大半个昆明城 , 停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大院里 。 已是晚十时 , 春城的这一部分 , 像是早早入了梦乡 , 看上去如同仓库的一扇扇大门闭得紧紧的 。 朋友显然是常来 , 深深的黑暗一点也挡不住他 , 三弯两拐就带着我们爬上那惟一还亮着“六大茶山”霓虹灯光的二层楼上 。
与别处不一样 , 坐下来好一阵了 , 还没有嗅到一丝茶香 。 女主人亲自把盏 , 边沏茶边说 , 她这里是不对外营业的 , 来喝茶的都是朋友 , 不过 , 有人意外跑来 , 她也一样当朋友待 。 女主人将几样茶具颠来倒去 , 听得见细流声声 , 也看得见眼前所摆放的那些据称价值连城的茶砖 , 熟悉的茶香却迟迟不来 。 天天十个小时以上的车程 , 又都是那别处早就消失了的乡村公路 , 确实太累了 , 小到不够一口的茶杯 , 不知不觉中已被我们连饮了十数杯 。 女主人很少说话 , 倒是我们话多 , 都是一些与普洱茶无关的事 。 女主人不时地浅浅一笑 , 那也是因为当地朋友对她的介绍所致 。 不知什么时候 , 心里一愣 , 脱口就是一句:这普洱茶真好!话音未落 , 寻而不得的茶香就从心里冒了出来 。
到这时女主人才露些真容 , 细声细气地说 , 不喝生茶 , 就不知道熟茶有多好 。 又说 , 刚才喝的是当年制成的生茶 , 而正在泡的是放了二十三年的熟茶 。 不紧不慢之间 , 一杯熟茶泡好了 , 端起来从唇舌间初一流过 , 真如惊艳 , 仿佛心中有股瑞气升腾 。 这感觉在思前想后中反复萦绕 , 不知不觉地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温馨念头生出来 , 在当时我就认定 , 普洱茶就像成就它的乡土云南的女主人 , 是冷艳 , 是沉香 , 是冰蓝 , 是暖雪 。 女主人继续温软地说 , 天下之茶 , 只有普洱可以存放 , 时间越长越珍贵 。 昆明地处高原 , 水的沸点低 , 在低海拔地区 , 水烧得开一些 , 泡出来的普洱茶味道会更好 。 听说由于温差所致 , 普洱茶在酷热的南方存放一年 , 相当于在昆明存放五年 。 我便开玩笑 , 将她的茶买些回去 , 五年后 , 不按五五二十五年算 , 只当作十五年的普洱茶 , 由她回购 。 一阵大笑过后 , 普洱茶的滋味更加诱人 。
推荐阅读
- 改姓氏需要什么手续
- 明星都在哪里整容?
- 去世的人能纹在身上吗?
- 网络暴力和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 淘宝银行卡怎么解绑?
- 狗狗一直在咳嗽干呕
- 赑屃是什么
- 口罩灭菌型和非灭菌型区别 口罩灭菌型和非灭菌型区别所在
- 狗狗吃狗粮拉稀
- 明月山机场在哪 明月山机场在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