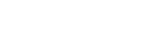文章插图
春上 , 我到长满茅草与马鞭草的山上植树 , 银锄落下, 吃进黄土 , 往上一提 , 错综复杂的草根便翻了出来 。 小时候 , 我是小小的放牛郎 , 生来十分馋嘴 , 却无物供应 , 于 是便趁放牛的闲散时光 , 手持一把盈盈一尺的小锄 , 专门 挖它们吃 。 茅根生长于地下 , 从没有见过阳光 , 滚壮肥硕 , 雪白透亮 , 尤其是那黄鳝怀孕样子的茅草根 , 水汁充沛 , 一嚼下去 , 滋滋出水 , 清甜淳厚 , 比糖果还甜蜜 。 再见茅根 , 如见故乡物 , 便挖了一大把 , 有大姐见此相问 , “你是拿回 去煎茶喝吧? ”这也可做茶喝吗?大姐说:“茅根当茶 , 特 别清火 , 对牙龈炎有奇效 。 ”天天生活在炎凉世界中 , 我经 常是一肚子火的 , 于是把茅根带回去 , 用砂罐子煎茶 , 茶 味不甜了 , 倒略略有点苦 , 吃那么三五次 , 牙龈炎果然好 了 。 这茅根有中药味道 。
我对茶的理解过去是过于狭隘了 , 以为要剃光头发才能是僧人 , 以为要端坐莲花打坐草蒲团才能是禅 , 以为从茶树上摘下的才能是茶 , 其实误矣 。 仁远乎哉?我欲仁, 斯仁已至矣;禅远乎哉?我欲禅 , 斯禅已至矣 , 仁无处不 在 , 禅无处不在 。 与人吵架 , 把嘴巴闭上 , 转身走开 , 斯 仁已至 , 斯禅已至 , 不一定非要上观音院 。 不茶之茶 , 我 是经常喝的 。 三五七八岁吧 , 我跟伢子们妹子们过家家, 从倒茶定亲到抬入洞房 , 虚拟了结婚的全套程序 。 其中倒 茶定亲 , 我们用的是干红薯叶 , 其叶圆 , 与展开的茶叶几 无二致 , 色泽亦无差 , 是那么一种茶褐色 , 用砂罐子泡 , 热气腾腾 , 奇苦 , 苦中有夹舌的涩味 , 我们大口喝 , 大口 笑 。 干红薯叶是冒牌茶 , 而我的童年也近乎是冒牌的童年 , 童年是无忧而甜的 , 我的童年很苦 , 当然是冒牌 , 童年的味道是干红薯叶的味道 , 我的童年是一杯苦茶 。

文章插图
实际上是 , 我喝过的许多茶 , 都不是茶 。 老家在遥远的小山村 , 山上多树多叶多草多花 , 藤蔓茑萝 , 花草枝叶 , 皆可入茶 。 喝得最多的是绞股蓝 , 母亲常常一篮子一篮子 地刈回来 , 晒干 , 包裹着 , 放在防潮防霉的谷箩里或米桶 里 , 多余的送人 , 余下的煮茶 。 后来 , 我吃过专门茶厂出 品的绞股蓝茶 , 说明书说得药用价值好得不得了 。 我看后十分开心 , 那样好的东西 , 我曾经像牛吃草一样 , 吃了那 么多 , 实在也是难得的福分与福气 。 现在我老婆经常给我 喝的是鱼腥草 , 这草药店有售 , 几块钱买得一大盆 , 春夏 之交 , 菜市上也有卖 , 不过是青草 , 特别腥气 , 简直有点 不可闻 , 没有喝习惯的人 , 无法入口 。 良药苦口 , 苦口者 大多是一片婆心 。 鱼腥草清目润脾 , 其功用有如“灭火器” , 心腹中的无名肝火旺熊 , 三五次当茶喝下去 , 火就剿灭了 。 生活是肝火的不灭活源 , 天天往人心里送火点火 。 血为什 么是红的 , 我想是心火烧的吧 , 血火一色 , 给我们激情的 同时 , 也给我们乱扑腾的情绪 。 老婆怕肝火伤人伤己 , 便 热衷替我买茶 , 特别喜欢买鱼腥草煎茶 , 鱼腥草算不上好 茶 。 好茶不好茶 , 能让人一身清泰一心清爽的便是好茶 。
我曾经到过临朝鲜临俄罗斯的延边 , 东北的饮食与南 方饮食迥然有异 , 我是一个南蛮子 , 嗜辣喜酸 , 无辣不成 菜 , 无酸不下饭 , 那边的菜都是甜腻腻的 , 我无法下咽 , 几乎半个月没有吃过一餐饱饭 。 但延边的茶却爽口 , 它非 叶子 , 非片片 , 是粒粒 , 茶汤淡紫带红 , 黄中见赤 , 喝下去 , 有炒熟的麦子滋味 。 我问老板娘 , 她说是麦芽茶 , 待麦子 发芽 , 将其烘干 , 炒老 , 就是麦芽茶了 。 每次用餐 , 我几 乎用之倒入饭中 , 咕哝咕哝连饭带水咽下 。 闻一多说:“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 ”闻先生写的是诗 , 当不得真 , 而在我 的人生旅程上 , 实实在在的 , 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
推荐阅读
- 皖是哪里的车牌 皖是哪的车牌号简称
- 夏朝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夏朝的政治制度有什么特点
- 缴纳社保有哪些好处
- 水果发霉了切除后是否能吃 水果发霉了切除后还能吃吗
- 洛阳牡丹节是什么时候
- 什么是蚕豆
- 倒挂金钟能养几年
- 微信如何注册
- 夏天开什么花
- 抖音如何取消视频作品的赞